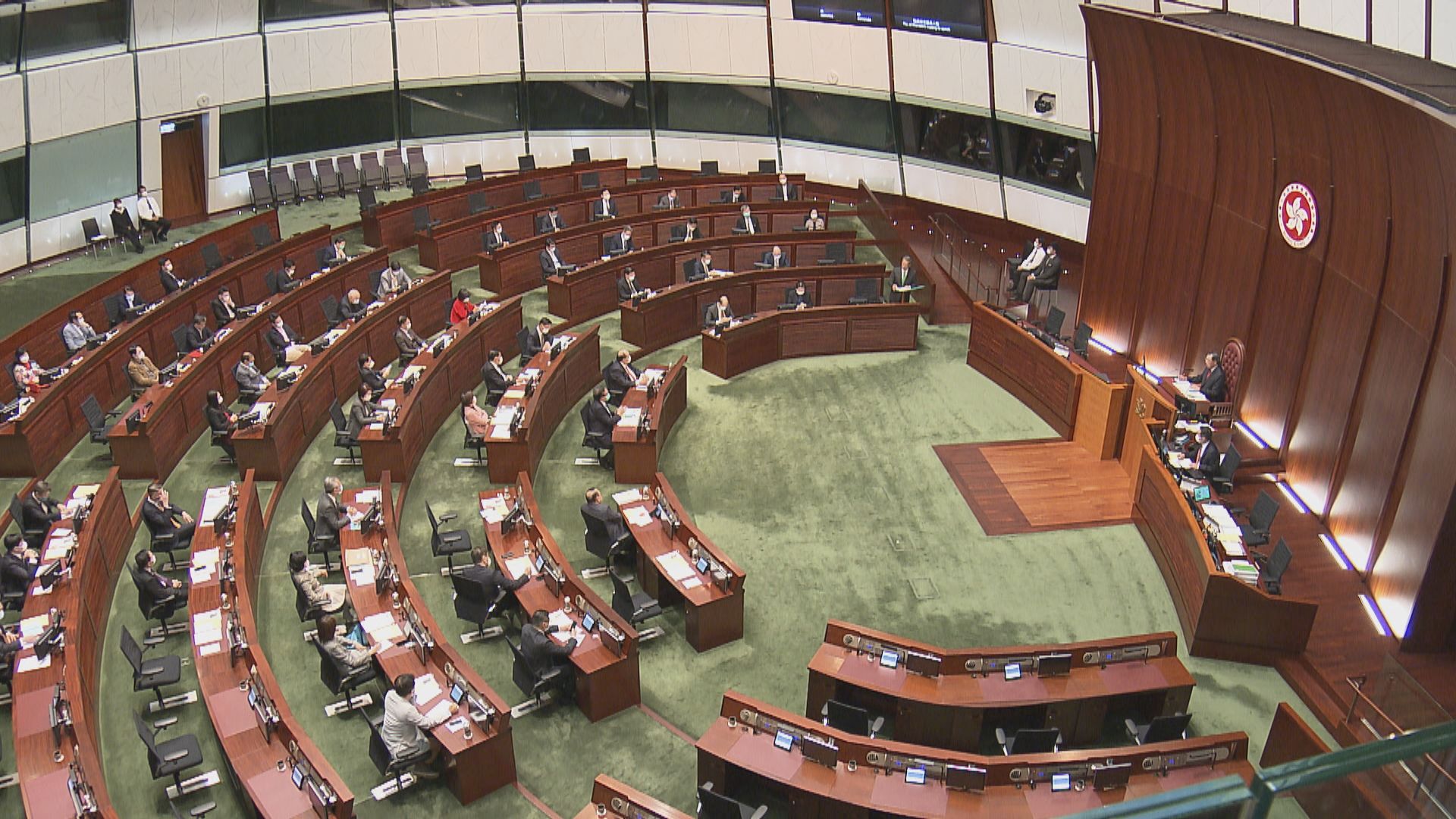訪談在隱密的香港郊區進行,接送我們的人分別是阿寶和Chris。他們都開著附有電動天窗的名車,2019年夏天以來,這些私家車頻頻出現在港人抗爭場合,不知接送了抗爭者幾趟。車上放了標準配備:水、飲料、食物、乾淨衣服,以便隨時因應突發狀況。阿寶和Chris在2019年的這場運動才認識,和許多受訪者一樣,他們都是現實中不生孩子、半年來卻照顧了許多孩子的「家長」。
他們稱自己的私家車為「校巴」,抗爭者不論年紀,凡被接送者都稱「小朋友」。11月18日,防暴警察在理工大學和勇武學生激烈對戰,中年人Chris就守在理工大學附近,接應了兩趟「放學」的勇武抗爭者。「好驚,他們的臉,真的好驚,」Chris記得,連續兩批勇武派年輕人上車後都是沈默,他一邊打著方向盤,從後照鏡中見到驚惶的臉,想問他們餓不餓?吃點東西好嗎?竟然開不了口。

「他們驚恐到連『你好』『謝謝』『再見』都說不出來了⋯⋯我能肯定他們的腦袋都是空白的。我找不到形容詞去形容那種驚恐的程度。沒有人在我車上哭。但是那一刻,我知道連吃東西都是奢侈的。」Chris彷彿也被感染了恐懼,「我一邊想,如果接送途中,我遇到警察截查,那我會被怎麼樣?」
傷心、感動、慚愧
他終究逃過了截查,確保了抗爭者和自己的安全。「我知道問他們什麼都沒有用,」他回憶那天晚上,「我只要他們感覺到安全就好⋯⋯我看到他們,覺得自己為香港付出太少了⋯⋯」訪談進行時,Chris的身邊還有一名自己負責接送的少年,少年沒哭,安靜不語,這名彪形大漢卻拔掉眼鏡痛哭起來,「最讓我傷心、最感動、也是最可以覺得自己做的,就是接送抗爭的寶寶,這也是我感到最慚愧的事情。」
「以前就覺得,我就是普通香港人囉,政治上沒有特別的角色,我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,但不關我的事,我不會理囉。」「我是從商的人,香港的繁榮,我也是既得利益者。一般我們這種人的想法,就是希望社會安定、穩定,才可以賺錢啊。」
他說自己活到40多歲,才知道有比賺錢更重要的事。Chris亦不諱言自己從來都是條港豬,那種不諱言帶著懺悔的意味:2003年,香港50萬人上街,抗議北京強推23條立法大遊行,他沒參加;近10年以來,每年七一、六四的紀念活動,他不曾到場;2014年雨傘運動,他去了現場,「以前覺得市民和人民力量從來不會改變什麼,但那時覺得人民的力量也許會改變什麼⋯⋯」隨著傘運失敗,他停止了對改變的想望;2016年魚蛋革命,他看了新聞,卻不曾前往現場。
他又嗚嗚地哭,「我們這一代,對所有東西都逃避,對政府很多事情都妥協,直到現在,下一代要承受我們當時妥協的後果,而他們承受的,又不知道是我們的多少倍。」
阿寶亦是個很成功的生意人,因為從商,結交的客戶來自三教九流,其中有不少警察或警眷。她有一對客戶,父母同為警察,孩子在校因而被欺凌、同學說「你爸爸是警察、殺人犯」,老師對孩子的態度也不好,孩子成天回家哭,最後被迫轉校。她常和客戶聊香港,得知許多警察的孩子也是抗爭者,「他們(警察)心裡很矛盾,但他們也都明白。」
阿寶的心裡也有諸多的矛盾和明白。她的父親在大陸出生,如今80多歲了,每天長嘆當年在大陸打仗,如今老了,香港情勢竟與打仗無異。阿寶的爸爸每天在唱〈願榮光歸香港〉,她和姊姊、姊夫都是負責接送勇武派抗爭者的家長。阿寶白天是商人,晚上還兼做急救員,為了不讓年事已高的爸爸擔心,他們很有默契的不讓家裡知道默默在做的事。

2019年11月,抗爭者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死守學校,與港警激烈衝突,阿寶就在場做急救。沒有醫療背景的她,一開始連用食鹽水替人洗傷口都會發抖,見到鐵彈沾黏在爆開的皮肉上,腦袋一片空白。是夜,她見到脫臼、骨折、燒傷、因遭水炮車射擊而引起的低溫症,最痛的莫過麻醉藥品用完,毫無外援,她必須協助在場醫護,讓受傷的抗爭者在未施打麻醉的情況下,當場縫合傷口。
「那是很痛很痛很痛的。」她哭著回憶,在場醫護無人不哭。但讓她更痛的記憶不止如此。阿寶在這場抗爭中與前線10名左右的孩子建立聯繫方式,她花了很多時間和孩子們取得互信,時常請孩子們吃飯。7月底,一名她認識的前線女孩被抓進新屋嶺扣留中心(拘留中心),雖然保全了性命,但不再回應阿寶的任何問題和訊息,亦不接電話。
一日,阿寶在臉書上看見女孩發文:「手足們:我堅持不下去了,你們代我撐下去吧。我會在另一個世界看你。」這是港人過去半年常見的發文,阿寶在恐慌之中到處找人,最後發現女孩自殺未遂。阿寶打聽了許久,女孩最好的朋友才說,女孩曾遭港警性侵,性侵的方式並非使用性器官,而是警棍。
「我為小朋友難過。」阿寶説,「他們沒有義務要承受這個問題。政府還說他們是錯的。很多小朋友都受傷了,(特首)林鄭還是說警察是沒有錯的,說警察沒有濫暴⋯⋯」
文章來源:https://www.mirrormedia.mg/story/20191231pol007/
以上內容皆為轉發,資料未經確實,只供備份參考。上述內容並不代表本站立場


![[警世]時事台法師食人血饅頭 (有圖)](https://aibeecom.tw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12/HIHIG-已修復-已修復-已修復-已修復-已修復-已修復-已修復-已修復-已修復-13.jpg)